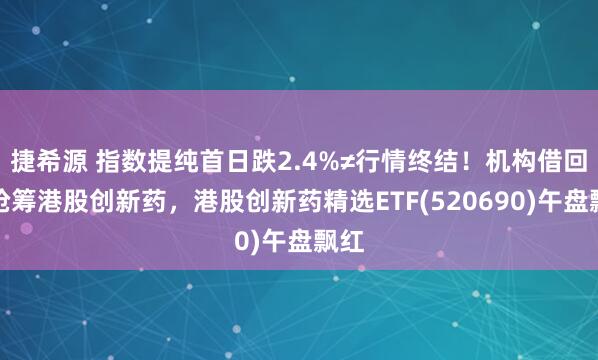最近又把《父母爱情》刷了一遍,看到江亚菲在医院里红着眼眶跟王海洋吵架,突然想起她妈安杰当年在岛上晒着太阳织毛衣的模样——同样是被生活推着走A策略,安杰总能把日子过成诗,江亚菲却总像攥着一把扎手的刺。
这母女俩,一个是从资本家小姐熬成的"老小孩",一个是在蜜罐里泡大的"小钢炮",怎么就活成了两种通透?我翻着剧里的细节,又想起她们一起经历的那些鸡毛蒜皮,这才慢慢理出点门道。
一、江亚菲的"不逊色":她本该活成另一个安杰
先说说江亚菲的"底色"。这姑娘打小就透着股子机灵劲儿。小时候在岛上,安杰嫌江德福说话粗,她跟着学文绉绉的"安老师";江德华煮的饭她不爱吃,她能举着筷子跟姑姑理论"这不是粗粮是硌牙";家里五个孩子闹成一锅粥,她能把弟弟妹妹管得服服帖帖,连江德福都夸"亚菲是咱江家的大管家"。
长大参加工作后,她的能力更显山露水。当护士时,她能把病房管得井井有条,病人家属都爱找她;后来当护士长,手下二十多个护士,谁偷懒谁用心她门儿清;连退休后给父母当"传声筒",她都能把江德福的"大老粗要求"和安杰的"小资讲究"调和得妥妥帖帖。
展开剩余86%论能力,她不比安杰差——安杰当年在岛上学挑水、学生火、学跟江德华斗智斗勇,江亚菲可是在更顺的环境里练出了"管家"本事。
论心气儿,她也跟安杰像一个模子刻的。安杰一辈子讲究"仪式感",喝咖啡要成套的杯子,吃饭要铺桌布,江亚菲也有自己的"讲究":给安杰买的面霜必须是上海产的,给江德福织的毛衣针脚必须密实,连弟弟妹妹找对象,她都要把对方的家世人品打听个底儿掉。
她甚至比安杰更"硬气"——安杰当年为了留在岛上,还得跟江德福"妥协"着过日子;江亚菲呢?跟王海洋谈恋爱时,对方是高干子弟又怎样?她偏要"我不图你家什么";离婚后独自带孩子,她也没掉过一滴眼泪。
可就是这样一个"不逊色"的江亚菲,怎么就活不出安杰那种"云淡风轻"的通透?
二、安杰的通透:是被生活"磨"出来的圆
要明白江亚菲的"卡壳",得先看看安杰的"通透"是怎么来的。
安杰的前半生,是被生活"揉"过又"展平"的。她本是资本家小姐,会弹钢琴、读外国小说,却因为出身在特殊年代吃尽苦头。
刚上岛那会儿,她连厕所都不敢去,嫌味儿大;看见江德华的粗布衣服,她皱着眉头说"这能穿吗";江德福说话带脏字,她能跟他冷战三天。
可日子久了,她学会在煤炉上煮咖啡,用搪瓷缸子喝出仪式感;江德华给她带野菊花,她能笑着说"这花插在玻璃罐里倒好看";江德福在院子里打拳,她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织毛衣——不是她妥协了,是她终于明白"日子是过给自己的,不是过给别人看的"。
她的通透里,藏着三次"和解"。
第一次是和出身和解:从"资本家小姐"到"江德福的媳妇"A策略,她不再把"讲究"当铠甲,而是变成让自己舒服的底气;
第二次是和婚姻和解:她看透了江德福的"粗"里藏着的"实",所以他忘记结婚纪念日时,她会笑着说"老江,今天该请我吃红烧肉";
第三次是和年龄和解:头发白了,她不戴假发,说"白头发多显气质";腿脚不利索了,她坐在轮椅上指挥江德福"把我的咖啡杯擦亮点"——她早把"在意"活成了"不在意"。
这种通透,是被岁月的砂纸磨出来的。她经历过物质匮乏,所以懂得"有一杯咖啡就喝,没有茶也能解渴";她经历过人际龃龉,所以明白"跟江德华置气不如教她认两个字";她经历过生死无常(江德福生病那次,她在医院守了七天七夜),所以看透"夫妻一场,能拌嘴就是福"。
三、江亚菲的"卡壳":她缺了那把"磨"的砂纸
可江亚菲没赶上这把"砂纸"。她的成长环境,是安杰和江德福用半生心血搭起来的"温室"。
1. 她的"被保护",让她少了"向下看"的视角安杰当年在岛上,要跟江德华抢厨房,要跟邻居解释"我不是地主婆",要在物资匮乏时变着法儿给孩子改善伙食。
江亚菲呢?她出生时,江德福已经是团级干部,家里有保姆做饭,有司机接送;上学时,安杰怕她被欺负,特意给老师塞了自己织的毛衣;工作后,江德福的老部下见了她都得喊"亚菲同志"——她从小到大,没尝过"求别人"的滋味。这种"被保护",让她的"讲究"少了份"共情"。
安杰的讲究是"我知道苦,所以要给生活添点甜";江亚菲的讲究更像"我习惯了甜,所以看不得苦"。
比如江昌义来认亲那会儿,安杰虽然生气,但看江昌义穿得单薄,还是偷偷塞了件毛衣;江亚菲却直接拍桌子:"他算哪门子哥哥?"安杰劝她:"孩子也不容易",她梗着脖子说:"他不容易关我什么事?"她不是不善良,是没经历过"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打乱"的疼。
安杰被江德华"抢"了厨房时,气哭过;被邻居说"资本家小姐摆谱"时,躲在屋里掉过眼泪;可这些疼,最后都变成了她眼里的"人间烟火"。
江亚菲没这些疼,所以她的"硬气"里,总带着点"理直气壮"的尖锐。
2. 她的"责任感",让她多了份"放不下"的执念江亚菲是家里的"长姐",这身份像块烙印,刻进了她的骨头里。
小时候弟弟妹妹打架,她得拉架;江卫民要去农村插队,她偷偷塞了二十块钱;江卫红谈恋爱被男方欺负,她带着王海洋去"理论";连江德福和安杰老了,她都要当"裁判"——老头要吃红烧肉,老太太说"胆固醇高",她得两边劝;老头偷偷给孙子塞零花钱,老太太要"审问",她得打圆场。这种"长姐"的责任感,让她活得比谁都累。
安杰当年也操心家里,但她懂得"退一步":江德福要接江德华来,她闹了几天别扭,最后还是给腾出了屋子;孩子们要去插队,她抹了把眼泪说"去吧,别惦记家"。
江亚菲却总像根绷着的弦——卫民回岛开茶馆赔了钱,她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,还跟王海洋吵架:"我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!";卫红离婚后搬回家住,她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,自己睡沙发,安杰劝她"别太较劲",她梗着脖子说:"我是大姐,我不管谁管?"她的"放不下",其实是安杰的"放得下"的反面。
安杰看透了"孩子有孩子的命",所以江亚宁去大西北,她虽然担心,却没拦着;江卫民要辞职,她虽然不理解,却给包了饺子。
江亚菲没看透这层——她总觉得"我是大姐,我得把他们都护在身后",可护得太紧,反而让自己困在了"大家长"的角色里,忘了自己也是个需要被疼的女人。
3. 她的"时代",少了份"慢下来"的从容安杰的通透,还沾了时代的"慢"。
她在岛上的三十年,日子是"日头从东边升起,西边落下"的慢;是"江德福下班回家,先喝口茶再吃饭"的慢;是"孩子们寒暑假回来,围在桌前听她讲上海旧事"的慢。
这种慢,让她有时间把日子"嚼"出滋味:咖啡渣晒干了装枕头,旧毛衣拆了给孙子织坎肩,连和江德华斗嘴,都能变成"今天她多放了盐,明天我少放把米"的情趣。
可江亚菲赶上的是"快"时代。她参加工作时,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岛上,医院要改革,护士要考职称,她得一边上班一边读书;结婚后,王海洋要下海经商,她得一边带孩子一边帮着打理公司;退休后,孩子们要去大城市发展,她得跟着搬家,适应新环境。
这种"快",让她的"讲究"变成了"赶趟儿"——给安杰买的面霜,她选最快的快递;给江德福织毛衣,她嫌手织太慢,买了台织机;连陪父母聊天,她都总看表,怕耽误接孙子放学。
时代的"快",让她少了"慢品"生活的心境。安杰能坐在院子里看一下午云,江亚菲却总觉得"有事儿没做完";安杰能把和江德福的吵架写成"老江今日又犯浑"的日记,江亚菲却觉得"吵架太浪费时间,不如直接说解决方案"。
她不是不热爱生活,是生活的节奏推着她,让她来不及"停下来,看看身边的风景"。
四、通透从来不是"活成谁",而是"活成自己"
可话说回来,江亚菲没活成安杰的通透,又有什么要紧?安杰的通透是"看山还是山"的圆融,江亚菲的"不通透"里,藏着另一种珍贵——她的直率,让江家兄弟姐妹有了主心骨;她的硬气,让王海洋明白"娶了个能撑得起家门的媳妇";她的"较劲",让安杰和江德福在晚年还能感受到"被需要"的幸福。
那天看剧的结尾,安杰坐在轮椅上,江亚菲蹲在她跟前给她剪指甲。安杰摸着她的头说:"亚菲啊,你跟我年轻那会儿真像。"江亚菲笑着说:"妈,我可没你那么会享福。"安杰说:"傻闺女,你有你的福。"
是啊,安杰的福是"把日子过成诗",江亚菲的福是"把日子过成火"——诗有诗的静美,火有火的热烈。通透从来不是活成某个人的模样,而是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。
江亚菲没活成安杰的通透,但她活成了江亚菲的"痛快"——这痛快里有对家人的热,有对生活的真,有不向岁月低头的韧。这样的人生,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?
#深度好文计划#A策略
发布于:福建省长宏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